史林折枝|福州書院與朱熹的深厚淵源
2025-04-11 16:17:35 來源:福州新聞網
書院作為我國獨具特色的教育與文化機構,起源于唐代,綿延逾千年,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持續創新的重要標志,為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。福建省擁有豐富的書院文化資源,例如,漳州松洲書院始建于唐代景龍年間(707—710),早于長安、洛陽兩京的麗正、集賢書院十余年,被湖南大學鄧洪波教授譽為“中國第一所教學功能比較齊全的書院”,在書院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。清代的鳳池書院、正誼書院、致用書院亦聞名遐邇,培養了眾多人才。鰲峰書院自1707年創辦以來,孕育了林則徐、陳寶琛等杰出人才,培養出163名進士、700多名舉人。作為八閩首府的福州,其書院資源在全省名列前茅,據2017年福建省圖書館普查顯示,清光緒三十二年(1906)以前修建,現存遺址、遺跡或經過重建、修繕的福建書院有207處,其中福州便有31處,僅次于南平。
 鰲峰書院舊址
鰲峰書院舊址
福州書院之所以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,與多種因素息息相關。若從歷史人物的淵源角度來探究,我們不難發現,南宋時期著名的理學家、教育家朱熹與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。朱熹不僅在學術上有著卓越的貢獻,而且在教育領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記。可以說,朱熹對福州書院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,他的思想和教育實踐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朱熹福州行跡概覽
朱熹,這位著名的南宋理學家,雖然出生在尤溪,但他的一生中卻多次踏足福州,并在福州進行講學和著述活動,極大地促進了當地書院的繁榮發展。在南宋紹興十二年(1142),年僅13歲的朱熹跟隨他的父親首次來到福州,其間拜訪了諸如程邁、傅自得、張元幹等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,從而開啟了他與福州之間不解的緣分。成年后的朱熹再次訪問福州,紹興二十三年(1153),當時24歲的朱熹正前往泉州同安縣擔任主簿一職,途中經過福州,拜訪了包括李樗、林之奇、劉藻、任文薦等在內的幾位當時極具聲望的學者。隨后,朱熹又因多種事宜,頻繁出入福州。據不同學者統計,朱熹一生出入福州竟然有十余次之多!不過,由于利用文獻的不同,一些福州朱熹行跡學界還有所爭議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“慶元黨禁”朱熹行跡。
“慶元黨禁”時韓侂胄執政,斥道學為“偽學”,不久寧宗下詔,訂立偽學逆黨籍。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,受此影響,朱熹避亂歸閩。關于朱子“慶元黨禁”期間的行跡,張品端認為朱子“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建陽考亭、滄州精舍講學,著述立說,曾幾度外出順昌、泰寧、建安、政和、崇安五夫等地,時間都非常短”。近年關于朱子生平的研究成果,也多表明朱熹“慶元黨禁”時期主要居于建陽。當然,也有一些反對意見,最近的研究成果中,高令印、薛鵬志利用大量福建方志考證,認為朱熹在“慶元黨禁”時期“避跡無定所”,曾數次逃到福建各地避難。
 鰲峰書院舊址
鰲峰書院舊址
實際上,通過福州方志記載可見,其為避“偽學”之禁流寓福州多日:“趙汝愚守福州,時熹避偽學禁入福州,名山勝跡,杖履殆遍,若鼓山、方山、烏石、鳳丘諸處,皆有題刻,至今存焉。”許多福州縣邑都有朱熹行跡,試舉幾例如下:
1.閩縣:“鐵冶場,在龍逕溪傍。《閩書》:‘朱子以避偽學禁,至此。’”
2.長樂:“紫陽樓,在二都后灣,元應宮之東。宋嚴學禁,朱文公避地于此,故名。”
3.連江:“慶元間,嚴偽學之禁,朱文公避跡至連,入安中里仁山留數日,主人禮奉甚周。”
4.古田:“慶元間,韓侂胄禁偽學,游寓古田。”
5.閩清:“朱文公于偽學之禁,避跡無定所。其于閩清,凡數至,所歷名勝題識殆遍,如廣濟巖之‘溪山第一’、白巖之‘八閩岳祖’,皆其親筆,現勒石尚存。”
朱子出入福州之時熱衷于講學授徒,亦見載于不少方志。如《(萬歷)古田縣志》稱:“宗室諸進士與其門人構書院,延而講學。”如螺峰書院:“在九都坑。宋時建。朱晦翁與黃勉齋曾講學于此,今廢為田。”藍田書院,《(民國)古田縣志》稱:“在杉洋北門外,朱晦翁書‘藍田書院’四字勒石……距書院左邊數武有聚星臺,相傳宋韓侂胄禁偽學時,晦翁嘗潛居此處。”據20世紀80年代于古田挖掘出的朱熹手書“藍田書院”“引月”“聚星”等石刻,可見方志記載有一定的可信度。
縱觀歷史長河,我們可以發現,成年后的朱熹,在途經福州的時候,不僅致力于結交那些資深的學者和儒學大師,而且更加注重將知識的傳授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使命。他頻繁地往來于福州及其周邊地區,每到一處,便積極與當地士人交流學術心得,共同探討儒家學問的精髓。無論是官方學府還是民間書院,都留下了他講學的足跡。
朱熹與福州書院
今眾多文化學者撰文闡述朱熹在福州創立了眾多理學書院,其中尤以紫陽書院最為著名。紹興三十二年(1162),福州知州汪應辰邀請朱熹至福州,朱熹遂在此地創辦了“紫陽書院”。由于朱熹曾自號“紫陽先生”,為紀念朱熹在此地的教育活動,該地被命名為“紫陽村”,即現今的紫陽社區。然而,筆者查閱現存的福州地方志,并未發現有關朱子創建紫陽書院的記載,亦未見其他書院的創建記錄。盡管如此,正如前文所述,朱熹在福州期間致力于講學,培養了大量理學人才,使福州成為全國理學的中心之一。因此,朱熹成為福州書院的重要文化象征,許多書院專門設立朱子祠以示祭祀。
朱熹在福州的門人中,以古田籍者居多。“慶元黨禁”期間,林用中等古田籍門人懇請朱熹至古田講學以避黨禁。據地方志記載,朱熹流寓古田期間,曾在溪山書院講學,并題寫“溪山第一”。后世以此地為朱子祠,并以邑人林用中、林允中配祀。林用中、林允中亦為朱熹的高足,特別是林用中,曾隨朱熹參與“岳麓會友”“鵝湖之會”兩次理學盛會,理學成就卓著。嘉靖年間,古田發生大水,書院因此毀壞,文公祠亦不復存在。萬歷年間,歸安王繼祀掌政古田,在文昌祠之側,故射圃地改建新祠。余文龍對此大加贊賞:“此宜合享新祠,以孚輿論。且俾見而慕,慕而奮,以能自得師,士習蒸蒸,從此盛焉。即吏茲土者,及過而游者,無不油然動先賢之仰而景行自新。”由此可見,朱熹對福州文化的影響深遠,邑人對朱子的敬仰之情,并未因書院祠堂的毀壞而消減。
朱熹,這位南宋時期的著名儒家學者,他的講學活動不僅影響了當時,而且其講學過的書院,也成為后世福州學子向往的圣地。在前文提及的古田溪山書院,是朱熹與林用中兄弟共同講學之所,吸引了眾多士子前來觀覽、學習。如《過溪山書院》一詩中寫道:“由來閩學自相承,古邑儒風信足征。郭外溪山看似昔,水邊輪奐□重興。新苔點點蒼痕厚,榮木欣欣翠色凝。先喆英靈全有托,夜深猶見讀書聲。”該詩末句“先喆英靈全有托,夜深猶見讀書聲”富含深意,不僅與首句“由來閩學自相承”相呼應,也運用通感手法表達了對朱子的敬仰之情。詩中所描繪的景象,不僅反映了溪山書院的學術氛圍,也映射出朱熹及其學派對后世深遠的影響。
在士子們的追慕和官方的倡導下,許多朱子祠不僅成為紀念朱熹的場所,還兼具了書院的功能,成為傳授知識和文化的重要中心。例如,連江九龍山的朱子祠,就是在知縣李毓英的主持下,應眾多學子的請求,將原本的淫祠改祀為朱文公的特祠。正如《(乾隆)連江縣志》卷一二《書院志》中所記載:“圣朝崇理學,敕郡邑建朱文公特祠,典誠巨也。連為公經游地,祀事獨闕。歲戊寅,郡侯遲公維城,飭毀淫祠。邑治南舊有廟當毀,諸生請于邑侯李公毓英,改祀文公。侯曰:‘吾志也。’力請檄行,因而更新之,廟貌肅然。”這段文字記載了當時士子們對朱子的崇敬之情,以及知縣李毓英對這一轉變的支持和努力。許多學者在此地講學授徒,吸引了眾多士子,“東西舍生徒恒滿”生動描繪了士子聚集求學的場景。該祠后來也改建為書院,成為一個學術氛圍濃厚的教育機構。朱子祠與書院的轉化,不僅體現了后人對朱子的尊崇,更表明朱子作為一種精神象征,深刻地烙印在福州士子的心中,成為他們學習和追求知識的不竭動力。
朱熹在福州的活動,不僅推動了福州書院的興盛,也使福州成為南宋理學傳播的重要中心。他將教育、學術研究、人格的培育以及文化傳統的傳遞這四個方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,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教育理念和實踐方式。他的講學、著述和教育理念,深刻影響了福州的文化教育,培養了大批理學人才。朱熹與福州書院的深厚淵源,不僅是福州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,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頁。
- 《下飯江湖》系列重磅回歸!第四季《食色福州》正式開機,探秘閩都千年煙火味(2025-04-11 16:14:23)
- 家書兩岸 思念成海!福建海洋文化創意展在榕開展(2025-04-11 16:06:14)
- 來福州“簪”福氣:三把刀里的一抹古典風華(2025-02-18 14:40:12)
- 福州動畫師巧“借”壽山石雕技藝 “雕”出《哪吒2》玉虛宮云紋(2025-02-18 14:38:43)
- 福州金魚新春展覽開幕 觀展有機會贏取金魚主題文創(2025-02-18 14:37:58)
 山水相依 人城交融
山水相依 人城交融 2025年度大片《高考尖兵》正式上映
2025年度大片《高考尖兵》正式上映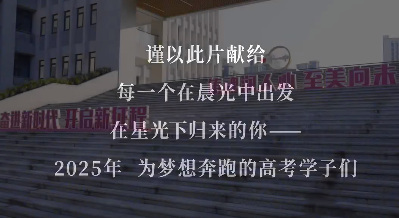 福州十一中:《逐夢星空》為高三學子加油
福州十一中:《逐夢星空》為高三學子加油 有福之州 以福為名
有福之州 以福為名 三山問好|今天是母親節,祝所有的媽媽們健康平安
三山問好|今天是母親節,祝所有的媽媽們健康平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