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與妻書》:情動(dòng)百年 流芳兩岸
2018-04-16 08:41:43 來源:福建日?qǐng)?bào)
林覺民的《與妻書》曾入選兩岸教材,是國(guó)人公認(rèn)的20世紀(jì)最偉大的情書和最感人的遺書。這封既是遺書也是情書的家書,一百多年來讓人們傾情誦讀,繾綣不已。近日,海峽姐妹雜志社采編室主任陳碧做客省圖書館“東南周末講壇”,與讀者分享《與妻書》承載的福建文化、福建人風(fēng)骨與精神傳承
作為生于斯長(zhǎng)于斯的土著福州人,陳碧近年致力于地方文化的挖掘與整理。她說,《與妻書》這封感人至深的家書,文如黃鐘大呂,情如杜鵑啼血,呈現(xiàn)出讓人敬佩的家國(guó)情懷。生與死,家與國(guó),愛與死亡,二者之間只能選擇一種,選擇哪一種都是情感上的悖論,都是人性人情中無解的大難題。所以《與妻書》很有看頭,也深入人心。也由此,林覺民成為人們心中鐵血柔情的英雄,而陳意映,這位從未走上社會(huì)的女性名字,成為千萬人反復(fù)誦讀的芳名。
《與妻書》寫作緣由
1911年辛亥廣州起義之前,孫中山曾領(lǐng)導(dǎo)十次起義,皆以失敗告終。
1911年春,黃興、趙聲在香港籌備廣州起義。留學(xué)日本東京的學(xué)生所組成的同盟會(huì)第14支部(即福建支部)開會(huì)研究,決定由林文去香港參與籌備廣州起義事務(wù),派林覺民回福建策動(dòng)響應(yīng)。林覺民突然歸來,他的嗣父感到驚異,一再追問原因。面對(duì)家人,在明知大概率要犧牲的情況下,他不能實(shí)情相告。林覺民這次回閩,就是動(dòng)員、選拔發(fā)難人以及后期策應(yīng)。志士們踴躍響應(yīng)。好友馮超驤也積極報(bào)名。馮母剛?cè)ナ啦痪茫涓赣植∥#钟X民勸他留在家中護(hù)理父親。馮超驤竟拔劍而起:“吾意已決矣,國(guó)事公也,家事私也;吾愛父之心,何嘗不百倍于常人,顧此時(shí)當(dāng)舍私從公。”其父亦從臥榻上強(qiáng)起說:“兒此去,為國(guó)努力,勿以吾為念。”其妻也在邊上發(fā)誓:“君趣去,萬一不幸,三月而后,茍無音耗,妾當(dāng)投繯相從于地下。”馮超驤當(dāng)即阻止妻子:“此決不可,家中上有老病之父,下有稚弟,我死罪已不可逭,卿若復(fù)爾,則仰事俯育,托之誰乎?”在場(chǎng)的人包括林覺民都感動(dòng)得流下眼淚。這件事也是后來林覺民要寫下遺書的原因之一。他生怕陳意映也如馮妻一樣,如果自己舉義犧牲,她也必將殉情。
林覺民一行去香港,轉(zhuǎn)廣州。在船上,林覺民對(duì)鄭烈說:“此舉若敗,死者必多,定能感動(dòng)同胞。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為救國(guó)惟一之手段,不可一日緩,特畏首畏尾,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。今試以余論,家非有龍鐘老父,庶母幼弟、少婦,稚兒者耶?顧肯從容就死,心之摧割,腸之寸斷,木石有知,亦當(dāng)為我墜淚,況人耶?推之諸君家族情況,莫不類此,甚且身死,而父母兄弟妻子,不免凍餒者亦有之。故謂吾輩死,而同胞尚不醒者,吾決不信也。嗟呼!使吾同胞,一旦盡奮而起,克復(fù)神州,重興祖國(guó),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。寧有憾哉!”當(dāng)晚,他們同宿在濱江樓,林覺民無法入睡,馮超驤別父別妻的場(chǎng)面一直在他眼前出現(xiàn)。他在別離親人時(shí),因?yàn)樗麄冞€蒙在鼓里,所以生離死別之痛,唯有他自知。他很難想象,如果在完全無知的情況下突然失去兒子,失去丈夫,又沒有片語只言的解釋和安慰,老父與愛妻將何以活得下去。所以,當(dāng)晚他分別給嗣父和妻子寫訣別書。
這一夜濱江樓的燈光遂成為永恒。拂曉,他將絕筆書托付友人:“我死,幸為轉(zhuǎn)達(dá)。”
盡見纏綿恩愛,又見志向懷報(bào)
陳碧說,現(xiàn)在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兩封信分別是《稟父書》和《與妻書》。后一信已成為海峽兩岸中小學(xué)語文教材,流傳甚廣。
《稟父書》寫在英文作業(yè)紙上,文曰:“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:兒死矣,惟累大人吃苦,弟妹缺衣食耳。然大有補(bǔ)于全國(guó)同胞也。大罪乞恕之。”寥寥41個(gè)字。從書法角度看其落筆處,情感飽滿濃烈,紙窄恨長(zhǎng),分為七行,前數(shù)行寫得慷慨激昂,第七行“大罪乞恕之”悲情畢現(xiàn),余音繚繞,仿佛情緒的悲憤糾結(jié)。
《與妻書》則選擇了日常的、帶著體味的一方手帕作載體,字體異樣地平靜,盡見纏綿恩愛,又見志向懷報(bào)。
“意映卿卿如晤”,剛開始的字跡如許平靜工整。他“抱定必死的決心”,寫下“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,吾作此書時(shí)尚是世中一人,汝看此書時(shí)吾已成陰間一鬼”。在強(qiáng)烈的悲憤情緒中,他仍努力控制自己,線條平鋪,仿佛在積蓄力量,要把信中所要說的事與情娓娓道來。所以前幾行,每個(gè)字的勾畫都是清晰的,包括“為天下人謀永福也”幾字,更顯坦蕩明亮。
第9行開始作回憶語,回憶夫妻兩人對(duì)話“誰先死”的問題,以及“入門穿廊”“又三四折”的后街之屋里的雙棲樓,以及與妻在冬望日前后恩情種種,筆底墨行處,婉轉(zhuǎn)流麗,深情款款。“吾與(汝)并肩攜手,低低切切,何事不語,何情不訴”一行,筆下忘情,每個(gè)字比前面的都大起來,讓這行的空間寬大起來,似乎讓情感再度有個(gè)流動(dòng)的轉(zhuǎn)圜場(chǎng)所。
“余心之悲,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,吾誠(chéng)愿與汝相守以死”一句,“悲”字“心”底哭泣,有“摧心肝”之痛。“誠(chéng)”字寫得穩(wěn)重凝練,有憂傷,有溫暖,還有在回憶中的沉溺。
第18行,“第以今日事勢(shì)”起,回憶破滅,語速一變,字速也一變。情感的把握漸脫離了最初的淡定,下筆便恣意、倉(cāng)促、快速了,字速漸漸加快。考慮到方帕的寬長(zhǎng)容量,而要表白的還有千言萬語,飽脹得要裂開的感情只好在筆墨里收縮,行草交錯(cuò)。
陳碧說,文中因有涂改數(shù)處,一般斷定是保留書寫者最初的自然狀態(tài)的墨漬筆痕,也因此被認(rèn)為是書寫者不經(jīng)修飾的即興創(chuàng)作。
惆悵悲傷,不失“詩意”
陳碧說,林覺民性情是當(dāng)遇知音時(shí),則“雅謔間作,涉口成趣,一屋傾倒”,可見是開朗的有趣之人,生平(可惜只有24年)“好游山水,幽蹤勝跡,歷訪無遺”,他曾是福建《建言日?qǐng)?bào)》主筆,可以說是豁達(dá)而有詩人情趣的。像他這種氣質(zhì)和修養(yǎng)的人,文章或許是他另一種層面的寄托。惆悵為文,悲傷下筆,甚至可以說信里的文字相當(dāng)“詩意”,這里寫的是一個(gè)有家有室,既溫柔又慷慨的男人——向親人流露內(nèi)心的思緒。惆悵或憂傷,并不總是灰暗與消極,也不會(huì)是豪邁和昂揚(yáng)的對(duì)立面。在《與妻書》中,它們反而使豪邁更為深沉,也因此,一個(gè)立體而豐富的林覺民才呈現(xiàn)于歷史煙云中。
這封信不論是文本上,還是每一筆書寫,都充滿了惆悵,如古人評(píng)書所云:深情綿渺,寄托深遠(yuǎn)。如果不讀文字,光是當(dāng)作書法作品,特別是前半部分,風(fēng)格顯得寧?kù)o與平和。因此,這不禁讓人揣摩,在起義前三天,要寫《與妻書》之前,林覺民一定打了又打腹稿,包括這封信的承載物方帕,都是事先想好的,用自己最常用的、貼身相隨的手帕。這手帕有著私密的意義,私密的情感,也許還有著私密的“體味”。
陳碧說,方帕在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特別是戲劇中出現(xiàn)時(shí),常是傳情達(dá)意的“媒人”。《與妻書》是典型的文人的文字,內(nèi)容也有著革命家情懷下文人式的纏綿。對(duì)林覺民文字的點(diǎn)評(píng)還有作家蘇雪林,她認(rèn)為林覺民的文字深受翻譯家、文學(xué)家林紓的影響。“一篇《與妻書》,自上世紀(jì)初以迄于今,又曾經(jīng)讓多少熱血青年,遙望黃花崗而‘扼腕墓道,發(fā)其志士之悲’哉!”此文讓她“一見鐘情,莫名感動(dòng)”。這封家書入選兩岸教科書,自有其文學(xué)意義與社會(huì)價(jià)值。
那一方手帕,雖何其軟柔,但一經(jīng)承載這些光輝照人的文句,變得可以立成一座豐碑,嵌入人們的心靈。
起義失敗后,林覺民被捕,后從容就義,史稱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”之一。
共和,民主,民權(quán),這些名詞已經(jīng)在林覺民和其他黃花崗烈士的無數(shù)舉動(dòng)里變成了動(dòng)詞。(林升文)
- 初三市質(zhì)檢5月16日開考(2018-04-13 15:11:47)
- 長(zhǎng)樂舉辦惠民資金網(wǎng)知識(shí)競(jìng)賽(2018-04-13 15:04:53)
- 話劇《縣委書記廖俊波》在京上演(2018-04-11 10:06:40)
- “吳清源杯”部分參賽選手已確定(2018-04-11 09:02:36)
- 第四屆海峽讀者節(jié)4月20日開幕(2018-04-11 08:57:29)
 山水相依 人城交融
山水相依 人城交融 2025年度大片《高考尖兵》正式上映
2025年度大片《高考尖兵》正式上映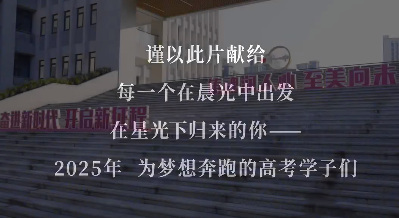 福州十一中:《逐夢(mèng)星空》為高三學(xué)子加油
福州十一中:《逐夢(mèng)星空》為高三學(xué)子加油 有福之州 以福為名
有福之州 以福為名 三山問好|今天是母親節(jié),祝所有的媽媽們健康平安
三山問好|今天是母親節(jié),祝所有的媽媽們健康平安